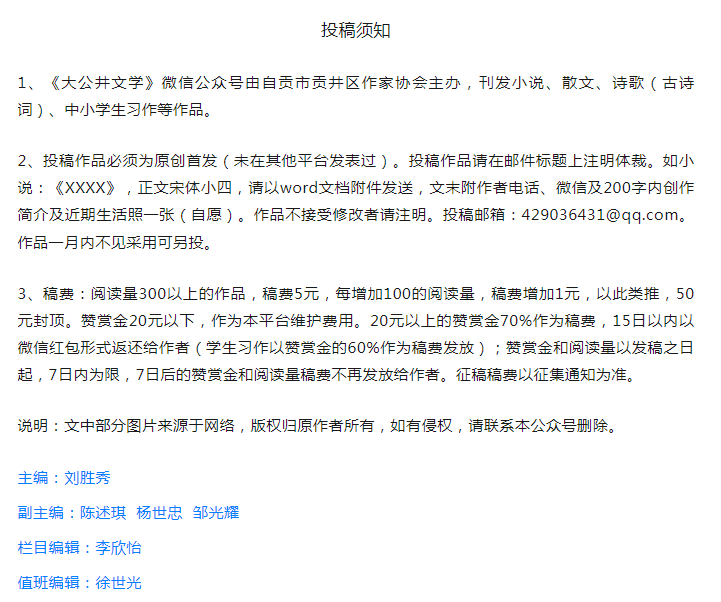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读一棵树,听一棵树轰然倒地的声音,才明白漫山遍野散布的,除了鸟语花香,还有生命的碎片。

一棵不再醒来的树
徐世光
几天前公园里贴了告示,将进行绿化整治,请游客注意安全。
从几十公里外搬到城里,也有二十多年了。我就像一棵草,习惯了乡下肥沃深厚的土地,在城市冰冷坚硬的钢筋水泥里难以扎根。难以扎根就飘着吧。你看公园里那些傲然挺立,一直遥望远方的大树,不也是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吗?
我们这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地方,本地植物生长茂盛,品种繁多。随处可见的东西并不值得稀罕。在有些人眼里,树如女人,别家的更漂亮。公园里载了一棵棵本地罕见的大树,还有好多叫不出名的奇花异草。好些年了,这些树的支撑仍然没有拿掉。时不时也有熬不过的,倒个底朝天。走近一瞧,那树根没有扎下去。

今天,我一如往常早早起床,到公园里逛逛。吹吹远道而来甜甜的清风,闻闻带着露水的花香,听听树巢里小鸟半梦半醒的情话。多年的习惯,改也改不了。小城的公园不大,当然也不算小。紧走慢走一圈下来,一个小时也是要的。
沿着公园步道幽暗的路灯漫步,偶尔身后窜出一两个跑者。呼哧呼哧冒出一串白烟,钻进了前面薄薄的雾色里。轻快的脚步声似乎唤醒了路旁的树。树们伸着懒腰,轻轻晃动着身子。一簇簇刚冒出的嫩芽,含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树枝无意间地晃动,无助的小水珠便纷纷滑落下来。一颗颗滴答滴答砸在花瓣上,藏进草丛里。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两束萤火虫般微弱的光亮,有节奏地左右摇晃。再移步向前,呼哧呼哧扫帚摩擦地面的喘息声越来越清晰。才六点一刻,这两个清洁工已经扫了好长一段路了。路面不宽,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动作麻利。另一边,略显矮胖一点的要迟缓些。高个子使劲挥几下,放慢脚步,抬了头,腾出一只手捶捶背。等矮个子赶上来再弯腰扫路。我不声不响地跟了几分钟。见矮个子手里的扫帚懒洋洋没了劲,高个子立了身子。一手杵着扫帚,一手擦着额上的汗。指着路边的石凳子招呼矮个子:“要不咱们歇一会再扫?” “师父,我们五点就开工,就是想早点把活做完,你好去看病。”矮个子也杵了扫帚擦脸上的汗。
“过来,坐坐,我们聊聊,等我走了,这片都是你的,有你扫的。”话没说完,已关掉头灯坐了半个凳子。我斜靠路边一棵大树上,佯装听耳机,她们的对话全跑到了我耳朵里。
“记住,早六点上班,晚六点下班。厕所值班室里煮饭时要把门关好。我们这里是没有休息日的,记得每天手机打卡三次。”
“你跟我这三天没工资的。等我结工资后我分一半给你。你也别叫我师父,扫地还用教?那是公司耍流氓,怕我撂担子。让你白干活。”不等矮个子坐定,她又吩咐着。
“哎!干这活,也得会想。秋天树叶满天飞,扫了又掉。我以前就边扫边骂树,树都死光了多好。经理说,没有树叶,没有垃圾老板请你们干什么?”矮个子这时也关了头灯,挨了过来坐在石凳上,握着扫帚听师父讲。
“你看,这公园里的树,和我们一样都是远道而来的。还有些树是几千里卖到了这里。它们有的生意盎然光鲜亮丽,就像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有的苟延残喘半死不活,跟我们一样,头发都白完了。老了没有养老金,找点吃点,累不动了,人家还不要你了。死不了又活不好,这种树爱掉叶子,最可恨也最可伶。”高个子讲着讲着,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慢。矮个子只是听,不答话。

我不由地摸摸身后的大树。树身到处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窟窿疙瘩。树皮干裂残缺,稀疏干瘦的枝丫凌乱地指向天空。刚长出的嫩芽,干瘪瘪显得有气无力。我不禁同情起这棵树来,伸出双手抱住它。
“最令人羡慕的树,你猜是什么树?”高个子突然转头发问。
“师父,我才来几天,我不知道。”矮个子望着师父一脸茫然。“最令人羡慕的树,是那棵倒下去,再也唤不醒的树,永远没有痛苦的树。我这次要是查出了重病,就回家挖个坑,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说着,高个子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往湖对面一指。我顺着方向看过去,一棵高大干枯的树倒在湖边。隐隐约约认得是棵来自遥远的南方的树,朝着它故土的方向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师父,大清早的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嘛。你没什么病,只是累了。辞工回去好好休息就会好的。你去医院看看吧,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矮个子起身收了师父的扫帚,拉师父往厕所那边去收拾了。

天亮开了,我静静地坐在石凳上。湖对面工人开始锯那棵不再醒来的树。呜呜呜是油锯的吼叫声,又仿佛是树的呻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