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公
常听人说:方面大耳的人有福。我不信,至少我从阿公身上看到了例外。
阿公是个孤儿,几岁就从老家来到邓关当学徒。那是在兵荒马乱的解放前,日子可以想见是如何的艰难。

不知阿公是怎样熬过来的,后来竟然在半坡头安了家,但好日子没过两年,阿婆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与伯父。那时,阿公在竹器社上班,天黑了,收工回来,还要在竹林旮旯里去找已经熟睡的孩子。既要忙着挣钱糊口,又要浆洗料娃,日子怎一个凄苦了得。
后来,阿公续弦了。之后,我多了一位叔叔。

打我记事起,阿公已经从竹器社退休了,每月领着几十元的微薄退休金。闲不住的阿公在家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大竹棚,又开始了竹器的打造。那时我觉得他好神奇。根根翠竹在阿公手中变成了凉席、箩筐、背兜、刷把……偶尔兴起还能编只小雀儿递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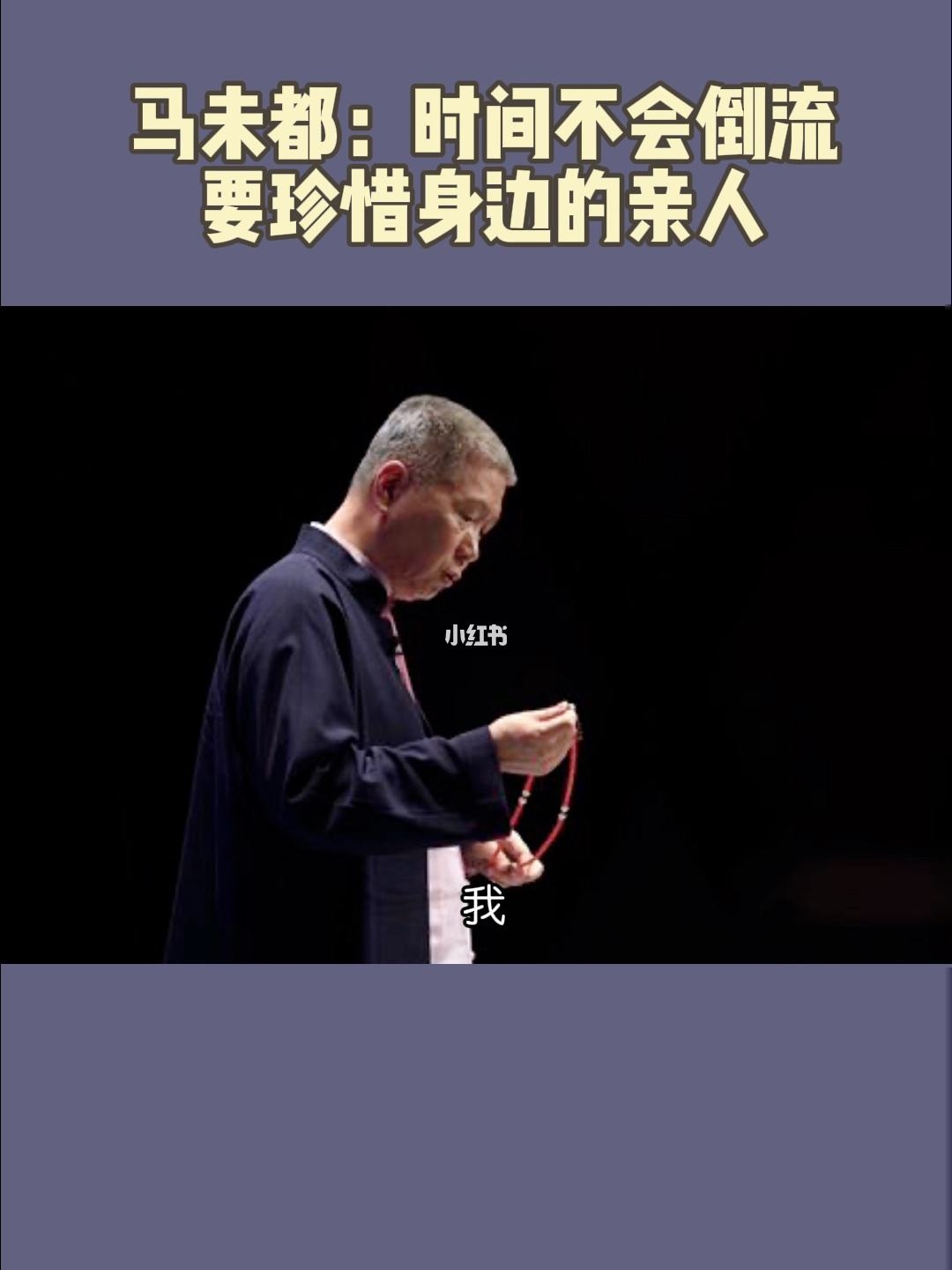
每年插秧后,阿公就要忙着编敞折儿了。那是插在半桶上打谷时必不可少的物事。每次经过竹棚时,阿公不是在分篾条,就是在编,忙得不亦乐乎。时间到了,还得回到前屋做饭。阿婆实在不擅这些劳作。
逢场的日子,阿公早早的就要带着阿婆去赶集,会扛上张张敞折儿去卖。这种时候,我和堂哥是满心欢喜的,半上午就会在塆子口翘首以盼。每次阿公都不会让我们失望,不是一个地瓜,就是一个泡粑,或是其他吃食。回来后,阿公开始了新一轮的劳作,我们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盼望。

慢慢的,阿公岁数大了,没有编敞折儿了。他的心思多半都花在照顾阿婆身上了,买菜做饭,浆洗衣服,打扫院子。阿公把阿婆照顾得无微不至。宅前院坝边,阿公砌了一个小泥炉,专为阿婆洗脚准备的。阿婆有脚痛的老毛病。夕阳余晖中,阿婆坐在藤椅上,双脚放入泥炉上装有草药的锅中。阿公细心地为阿婆搓脚,偶尔往炉里放一点儿柴火。那是一个多么温馨的画面。
那时阿婆喜欢拄着拐杖满塆子溜达,阿公做好饭后会到处寻她,再小心翼翼地牵她回去吃饭。当时,阿婆是村组上老婆婆们都羡慕的对象。

我工作后长期住校,每个周末才回家,见阿公他们的机会少。一次返家,我竟见阿公在翻盖老宅的瓦。当时,伯父和父亲他们都做事去了。可把我吓得紧,他已是70多岁的人啦。记得当时我还帮他递了下瓦,提醒他一定要小心。他说没事,还和我说了些话,大略意思是屋子漏了,要帮阿婆盖好。后来他又浆洗了满满一大桶衣服,提来让我帮他脱水。晚上父母回来时,我还向他们提到这个事。
然而,当晚阿公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大概是脑溢血这些。

转眼,阿公已去世20多年,我们做晚辈的也仅有每年清明去他的坟头缅怀一番了。亲人逝去了,只有越望越远。珍惜生者吧,有血有肉的,你的爱他们才能感受得到。若错过,仅余坟茔,空悲切,徒伤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