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科生到斯坦福,再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博士后,何世豪的医学之路被称为是“专升天”。
撰文 | 汪 航
责编丨汪 航
何世豪有两个“外号”:一个叫“专升天”,另一个是“何五点”。
从2013年至今,他从医学专科院校毕业后,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生、读博,之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再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博士后,求学经历堪称“开挂”。
风光背后,是他玩命般的拼搏。无论是读专科时借着厕所的明灯学到凌晨五点,还是备战考研时的艰难曲折,他都没有因为学历起点低而放弃对医学的追求,立志成为下一代顶尖神经外科专家。

何世豪
“拼了10年,终于把不敢想的梦想变成了我奋斗一生的事业。”何世豪希望,自己未来能在烟雾病的科研领域内贡献更多力量。
以下为何世豪的自述:
专科出身,
考上北京天坛医院研究生
我在高中是典型的差生,坐在班级最后一排,老师对我的期望是不要影响其他人上课。当时我喜欢玩游戏和看课外书,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要是考了倒数第二,可能是有一个人没来考试。
最后我的高考成绩是400分出头,因为不想复读,就报了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学医更多是受家庭影响,父亲是山东菏泽一家传染病医院的医生,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从小我就是在医院旁边长大,所以耳濡目染对医学更亲近。
刚上专科的时候,我开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临床案例课和实践课会很认真地听。但实话说,专科的整体学习氛围不是太好,刚开始我也会为了更合群一些,偶尔和同学们一起去网吧玩游戏之类的。
我们宿舍当时一共8个人。有一天,一个室友在玩游戏,旁边很多人围观,而我当时正在预习病理课,很多同学就说我“你挺能装啊”,因为他们觉得考试及格就行了。还有一次,室友凌晨三四点还在看恐怖片,我睡不着就开个小台灯学习,他们觉得氛围被破坏了,把我的台灯砸了、笔记本撕了。
这些嘲讽和排挤行为让我感到痛苦和压抑,但他们这样做反而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更想去证明自己了,而逃离的唯一方式就是专升本,我开始买本科的医学教材提前学习。
那段时间,宿舍晚上10点之后断电,我就带着小凳子到男厕所看1000多页的内科学教材,没桌子的话我就把脸盆扣过来当桌子用,一直学习到凌晨五点,两三年就那样过去了,当时同学们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何五点”的外号也由此得来。
三年专科生涯为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医学基础,专升本报考了泰山医学院(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虽然在几千人中只录取全省前100名,不过我特别有信心,最后也通过了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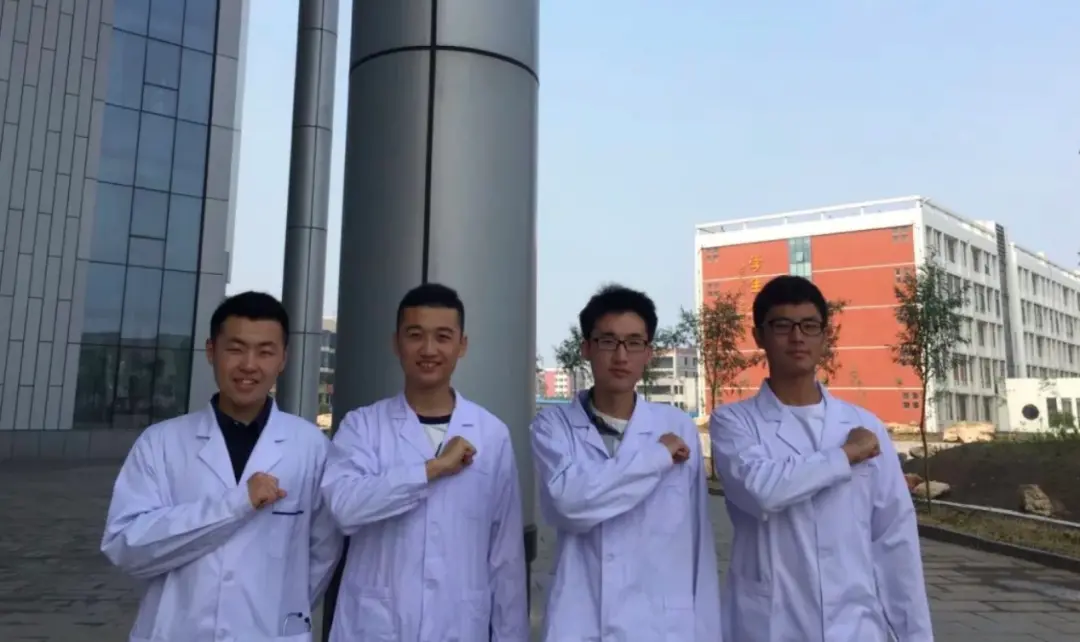
何世豪(左一)专科毕业
到了本科临床学习阶段,我接触到了神经外科,发现很多脑疾病的发病机制都不太清楚,这种挑战性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很早就计划考研了,而且瞄准了报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这家医院在国内神经外科领域排名第一。
考研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我们一个专业100人中也就有两三个能够考研成功,考上的基本也都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医学院,往届生中的考研天花板是南开大学,天坛医院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认知范围。当时有很多同学都不理解我的选择,认为我是痴心妄想。
刚开始我也没多少信心,中国大部分的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名校,招生简章都明确写了不接收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临床医学学生报名。我当时还用两个不同手机给招生老师反复确认自己有报名资格后才敢报考,并把画有天坛神经外科医生的一张海报贴到了宿舍床上激励自己。
为了考研,我在专科时的作息一直延续到了本科,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睡,早晨七点继续起来学,甚至一天最多睡3个小时。长期熬夜身体也出了问题,肝功能非常差,转氨酶最高超过了190,正常也就是10到40,去食堂闻见味道就恶心,就得找个垃圾箱去吐。
这么学下来,我对初试很有把握,但复试非常紧张,因为身边的竞争对手都是本科来自北大、兰大等985名校,我担心专科出身肯定是考不上了。为了放手一搏,在面试环节中的自我介绍、大外科提问和阅片等环节,我都是用英文来解答,现在看来是很大的加分项。
我还记得,录取结果念到第11个人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旁边另一位同学还给我递了纸巾,考上的人里面好像就我哭了,因为我从来没敢想过,自己能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一步步去天坛医院学习。
在天坛神外,决心研究烟雾病
考上北京天坛医院之后,我没有高兴太久,很快就又陷入焦虑中。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北京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嵘教授,在国内烟雾病诊疗领域首屈一指。在他的带领下,我开始踏足这一全新领域。
其实没去学校之前,我很担心导师对我的出身有顾虑,也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开学后的学习与工作,所以我连本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提前把宿舍的被子、衣服打包完,一个人坐上了从泰安到北京的火车,去天坛医院提前实习。
那时,同学们都在放暑假,我提前入组实习,一位师兄看到了我求学的积极性,就让我去重庆学习脑网络相关技术。越是学习,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我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提前对烟雾病领域进行了解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当时还积累了100多个病例数据。
烟雾病(MMD)是一种罕见的、慢性的进展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病因不明,临床表现为双侧颈内动脉末端慢性进行性狭窄或闭塞,脑底出现异常纤细的网状血管。烟雾病是我国儿童和中青年人群脑血管意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儿童缺血性脑卒中的年发病率高达7.9/10万,其中,因烟雾病导致的脑卒中比例约有22%。
当时,全国能做烟雾病手术的诊疗中心不超过五家,从事烟雾病诊疗研究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在缺乏有效识别方式的背景下,烟雾病也非常容易出现漏诊、误诊的情况。
确定研究方向后,我用了半年时间,把烟雾病相关的3000多篇文献全部下载下来,一点点研究。那段时间,我白天参加规培,跟着老师查房、换药、上手术等,只有晚上才能看文献和做课题研究,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看完这么多文献之后,我没有任何不自信的感觉了,虽然周围同学都是北大、协和、首都医科大学8年制的学生,但我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懂得多。后来,我还作为课题组的主导,去探究烟雾病的发病机制。
除了诊疗存在空白外,和导师的出诊经历也影响了我的科研走向。有一次,一位青年拿着档案袋来到了导师的门诊,他的右侧肢体像是有些脑梗残留的后遗症,在上一位患者就诊完毕后,他进门就说自己是来感谢王主任的。

何世豪与王嵘主任出门诊
原来,他小学时经常会在过度换气或劳累后出现右侧的肌力下降,有时还头晕伴有眼睛黑矇,一直没有就诊,直到出现一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以后,家人才重视起来。
当时他休学后四处求医,是王嵘主任结合影像学检查为他确诊了烟雾病,并通过血运重建手术和康复治疗后逐渐缓解。而他这一次来,是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后,专程来感谢我老师的。
也是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太过局限,也有专家说过,天坛医院培养的是医学科学家。我记得,硕士一、二年级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烟雾病认知损伤和手术风险评估等,慢慢开始转而探索烟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寻找更好的诊疗方案。
拒绝哈佛、梅奥诊所,
去斯坦福继续深造
在我第一年完成住院总的培训后,管理病人和参加手术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进一步去研究烟雾病的想法。加上我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四篇SCI论文,影响因子约有十二三分,顺利攻取了博士学位,导师是神经外科脑血管领域顶尖专家赵元立教授。
随着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血运重建手术能增加脑灌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卒中等脑血管意外的风险。然而,烟雾病患者发病年龄较动脉粥样硬化普遍年轻,其认知障碍状态持续发展时间要远长于动脉硬化患者,若不能及时评估及修复,势必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