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关于寺庙「关闭法物流通处」的传言越来越多了。
2025年12月,“雍和宫法物流通处可能关闭”“开光室将关闭”的消息在互联网流传甚广。截至目前,雍和宫并未公开回应过相关传闻。
2026年元旦,出于假期管理的需要,雍和宫依然保留了「节假日法物流通处不开放」的传统,但也因此被部分网友误读为雍和宫永久关闭了法物流通处。
雍和宫不是唯一一个陷入此类传言的寺庙。
此前,灵隐寺减少法物流通处柜台的做法,也被部分网友解读为或将关闭法物流通处的前兆。
2025年之前,寺庙的经营调整或许只是部分信众和游客关心的事情,但现在关于寺庙商业调整的蛛丝马迹,即便只是猜测,也可以激起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所有一切都被坊间解释为五个字:释永信余波。
虽然释永信本人已被批准逮捕并移送司法审查,但大众关于宗教腐败和寺庙商业化整改的关注却远未结束。
过去半年,佛门争议不断。
释永信被捕、“网红慈善僧”道禄因诈骗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五台山“扔米事件”引发公众信任危机......《凤凰周刊》曾跟踪报道过2025几大佛门争议,试图探讨:
佛教是如何进入「资本围城」的?
释永信之后,中国佛教界将如何处理宗教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
虽然目前看来,互联网上关于寺庙商业整改的讨论大多都无法被证实,但事情确实如网友们期待的那样:
宗教界的自我革新,正在悄然发生。
2025年的佛门并不清净。
从7月,执掌嵩山少林寺近30年的住持释永信,因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资产、违反佛教戒律被查,到11月,他正式被检方批捕;从6月“网红慈善僧”道禄因诈骗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到五台山“扔米事件”引发的公众信任危机——短短半年间,数个标志性事件接连爆发。
这不再是坊间传闻或是猎奇故事,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宗教领域反腐攻坚战。
当僧人的信仰与商业资本重叠,当“慈悲”成为一种生意,监管的雷霆手段表明:宗教场所并非法外之地,信仰的特殊性不能成为逃避法律监管的护身符。
这场风暴,不仅揭开了千亿“寺庙经济”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更标志着中国宗教事务治理正在完成从“行政管理”向“法治化、规范化”的历史性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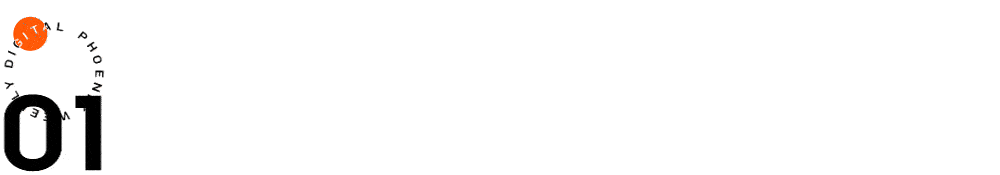
商业迷途
清晨六点的河南嵩山,薄雾未散,早课诵经声已然响起。僧人们身着杏黄色袈裟,双手合十,低沉悠远的梵音穿透殿宇飞檐,在山间缓缓回荡。
景区之外,画风截然不同。
停车场内,旅游大巴陆续停靠,导游高举小旗召集游客,人们攥着每张80元的门票,等候踏入寺院。不远处的文创店里,摆着印有少林LOGO的佛珠等纪念品,商业气息扑面而来。
去过少林寺的人或许都有同感:塔林、藏经阁、大雄宝殿虽庄重,但游客却可自由进出,并无太多神秘色彩。真正让外界感到神秘的,是位于寺院中轴线上的方丈室。相传清乾隆皇帝巡幸少林寺时曾在此居住,故又名“龙庭”。这里曾是前方丈释永信接待重要人物的场所,门口常年站着两个保镖。
2025年夏天,随着释永信被调查,千年古刹的平静被彻底打破。
这位执掌少林近30年的住持,曾一手缔造了少林的商业版图。他注册商标、组建武僧团,甚至推动公司化运作,被外界戏称为“少林CEO”。
然而,这种“以商养武、以商弘法”的模式,最终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权力封闭闭环中走向了失控。
武僧团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彼时,释永信带着弟子赴全国各地表演。这些融合禅意与武术的表演,让沉寂多年的少林功夫重新进入公众视野。1990年,武僧团首次出访海外,在新加坡的演出引起轰动,随后又赴美国、日本等地巡演,少林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1998年,释永信注册“少林寺”商标,涵盖武术培训、禅茶、素斋、旅游纪念品等多个品类,将少林文化与商业运营深度结合。2009年,经过多年谈判,少林寺与登封市政府达成协议,重新获得寺院核心区域管理权和门票分成。
在他的运作下,少林寺经济状况彻底改观:仅门票分成一项,每年就能获得约4000万元收入,周边武术学校、文化演出等相关产业,形成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链。寺院修缮了殿宇,新建了僧寮、禅堂、藏经阁,僧人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那个时期,释永信频繁出现在商业论坛、文化活动中,穿着袈裟使用智能手机,乘坐豪车出入。
这种“与时俱进”的形象,一度被视为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典范。

方丈落幕
释永信的商业化举措起初赢得不少支持,但随着商业化程度加深,争议也随之而来。
2009年,有媒体报道他的定制云锦袈裟估价16万元,仅金线就价值5万元,“天价袈裟事件”拉开负面争议的序幕。
2011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嫖娼被抓”的消息在网上传播,少林寺事务管理委员会向登封市公安局报案。同年10月,网传他在海外有30亿美元存款,在美国、德国等地拥有别墅,还与明星有染、包养北大女学生并育有一子,少林寺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这些是恶意编造的诽谤。
2015年7月,署名“少林寺知情人士释正义”的网帖《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热传,帖中称释永信有2个户籍和身份证,有情妇并通奸。少林寺发布报案材料,要求查处造谣者,释永信则表示“不辩解脱”。2017年2月,调查结果公布,网传七大问题均被证实有误。
更严重的争议来自佛教界内部。传统僧人认为,释永信的行为违背“四大皆空”教义,过度追逐名利与世俗化。有僧人批评,少林寺的核心应该是禅宗修行,而非商业炒作,如今人们只记得少林功夫,却忘了少林是“禅宗祖庭”。甚至曾有僧人在塔林拉横幅,控诉释永信挪用门票收入、排挤老僧人,引发轩然大波。
释永信始终辩解称,商业化是传承文化的手段而非目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利益的诱惑逐渐模糊了手段与目的的边界。
2025年7月26日,网上出现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凤凰周刊》记者拨打少林寺客堂电话求证时,对方始终关机,少林寺内多位法师回复“等官方消息”或“在外面学习,不清楚”,释永信的个人账号则定格在7月24日清晨6点58分。
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的通报证实了外界猜测: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资产、违反佛教戒律,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他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寺院资产,将部分收入用于个人挥霍,还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
这场持续二十年的争议,最终以释永信身败名裂告终。中国佛教协会在注销其戒牒的公告中称,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佛教界的声誉,损害了出家人的形象”。
对此,一位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官员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这就是权力异化,其本质是宗教腐败的一种形式。”他说,“这些宗教人员凭借身份获得的特殊信任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力’——信众因为相信宗教教义的向善性,进而信任践行教义的宗教人员。但当这种‘道德权力’被滥用,用来谋取个人私利时,就演变成了另一种隐蔽的腐败形态。”

失控的“慈悲生意”
如果说释永信代表了传统名刹的“资源型腐败”,那么江苏的道禄则代表了新型的“流量型腐败”。
这位被称为“和尚爸爸”的僧人,精准击中了社会痛点——未婚妈妈与弃婴救助。他利用社交媒体打造“慈悲”人设,绕过民政部门非法收养,在监管真空地带疯狂吸纳社会捐赠。警方查明,其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且多用于个人高消费。
道禄案暴露了宗教慈善在互联网时代的监管盲区:一个披着袈裟的“个人IP”,是如何在法律边缘通过兜售“善意”实现巨额敛财的。
道禄原名吴兵,1977年生于江苏南通如皋的农村。早年,他投身商海,开办工厂经营外贸工艺品,积累了不少财富。但物质的富足并未带来心灵的安宁,生意场上无休止的觥筹交错,让他渐渐生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1999年,吴兵的妻子怀孕,这段近亲婚姻让他陷入深深的焦灼,生怕孩子出生后存在健康问题。于是他走进寺庙许下承诺:若女儿能平安降生、健康成长,他将在五十岁后出家为僧,以报答“佛恩”。命运似乎回应了他的祈愿,女儿顺利出生且身体健康,可几年后,吴兵与妻子因生活分歧分道扬镳。
2010年,安顿好女儿的生活后,吴兵提前兑现了部分“承诺”——他来到厦门普光寺剃度出家,法号“道禄”。出家后的一两年间,他遵循僧人云游修行的传统,背起行囊走遍多地,2012年落脚南通普贤寺“挂单”(指云游僧人到其他寺庙请求投宿暂住)。
在寺中修行的这段日子,让道禄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偏转:他频繁遇到因堕胎而来做佛事的年轻女子,她们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的困境,也让他注意到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那些为未出世孩子祷告、满心愧疚与无助的香客。他因此萌生了“直接救人”的念头,不久后,他公开了个人联系方式,正式踏上了救助孕妇和弃婴的道路。
从接到第一位求助孕妇开始,道禄便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投入这场“救助”,全盘包揽了从待产到生产的所有事务:陪同孕妇到医院挂号缴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手术室外彻夜守候陪产……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消息逐渐传开后,求助者络绎不绝,在寺庙香客和居士的自愿协助下,道禄的救助范围不断扩大。2014年,一位女信徒主动提出帮忙,为他搭建了公众号平台,此后,道禄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海量求助信息,最多时,半年内就有七十多位孕妇带着希望找上门来。
他出家前在如皋为女儿购置的小楼,也被改造成了专门安置孕妇和孩子的救助站,道禄为其取名“护生小居”。
从2012年到2019年,道禄累计救助了超过300位孕妇顺利产子。2022年,他又将救助事业拓展到浙江一带,同年6月,他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注册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绍兴市上虞区莲花慈善社”,业务范围明确标注为“开展弱势儿童、孤儿、单亲困难孕妇救助等活动”,这让他的“救助”行为看起来更具“合法性”。
截至2025年被警方抓获前,据统计,他已累计收留超过1000名未婚妈妈,抚养了500多名弃婴。
起初,道禄的行为收获了一片赞誉。他还会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分享照顾孩子和未婚妈妈的日常:镜头里,是简陋的居住环境、孩子们略显破旧却干净的衣物,以及他们纯真灿烂的笑脸,这种“朴素的善意”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吸引了大量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和物资支持,也让这场民间救助显得愈发“正当”。
但随着救助规模不断扩大,这场“善意救助”背后的诸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首要的便是合法性缺失:无论是早期的“护生小居”,还是后来以慈善社名义开展的活动,收留未婚妈妈和弃婴的行为始终未经民政部门批准,属于典型的非法收养;同时,他接受的巨额捐赠资金缺乏第三方有效监管,资金流向不明的嫌疑日益凸显,外界无从知晓捐款究竟是用于救助对象,还是被挪作他用。
更严重的违规操作,在媒体的深入调查后被逐一揭露:
部分未婚妈妈在生下孩子后,会被道禄以“孩子能得到更好照顾”“你无力抚养只会耽误孩子”等理由劝说,最终“自愿放弃抚养权”。
这些被放弃抚养权的孩子,在道禄的“收养”名义下被随意安置,甚至有部分孩子被他转介给他人,从中收取“营养费”“安置费”,涉嫌变相买卖儿童;
他还利用“和尚”身份自带的道德信任光环,向求助的未婚妈妈收取高额“生活费”,即便对方经济困难也不例外;
更有证据显示,部分社会捐款被他用于个人消费,与他“清贫救助”的人设严重不符。
2025年6月25日,这场持续十余年的“救助神话”轰然崩塌。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有关部门对外通报,道禄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初步查证涉案人员共4人,涉案金额可能超过千万元。
同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公告,正式注销了道禄的戒牒,彻底剥离了他的宗教身份,从官方层面否定了他的“僧人”资格。
道禄事件迅速引发全社会热议,核心焦点集中在“宗教慈善边界”这一关键命题上。
支持者认为,道禄的初衷源于纯粹的善意,在社会救助体系尚未完全覆盖的领域,他的行为填补了部分空白,切实帮助了那些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不应仅凭后续的违规就全盘否定其早期的贡献;
反对者则坚定主张,宗教慈善并非法外之地,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任何善意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合法合规是慈善事业的前提,一旦脱离监管,善意很容易被异化,最终酿成更大的伤害。

资本围城
宗教腐败的滋生,并非一日之寒,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宗教活动场所实行“自养”政策。彼时,这一政策旨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帮助历经动荡的宗教场所恢复运营,寺庙通过门票、香火、素斋获取收入的模式被合法化。
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解困之举”竟成为宗教商业化的起点。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将宗教旅游视为拉动经济的“香饽饽”,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资本随即大举入场。
当商业逻辑强行嵌入千年的清修体系,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2025年6月下旬,五台山中台演教寺的风波,正是这种体制性张力的极端体现。视频中,僧人释某道将信众供奉的米袋狠狠掷出殿外,怒斥信众“不懂规矩”。这一幕瞬间引爆舆论,网友纷纷指责出家人“慈悲尽失”。但剥离情绪化的指责,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的正面相撞。
事件的起因简单却讽刺:按照中台演教寺的规定,信众的各类供养需统一在文殊殿接收,这是寺院为规范宗教活动、维护场所秩序制定的基本规则。
但当天,一名由其他僧人带领的信众,却坚持要在天王殿完成供米仪式。
守殿僧人释某道上前劝阻,双方随即发生争执。据现场视频显示,争执过程中,信众坚持要在非规定区域供米,理由是“花钱来拜佛,想在哪里供就在哪里供”。
而在僧人释某道眼中,寺院首先是“戒、定、慧”的修行道场,其次才是接待场所。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五台山不仅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更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数据显示,仅2025年前三季度,五台山游客量就逼近600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带来了可观的门票分成和香火收入,也带来了喧哗、打卡和无尽的世俗干扰。
这场争执的最后,释某道情绪逐渐失控,做出了扔米怒斥的过激行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释某道的爆发,实则是僧人长期在“清修需求”与“景区KPI”夹缝中生存的压力释放。当寺庙被赋予了过重的经济功能,僧人被迫兼职“导游”或“服务员”,这种身份的错位,既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也为冲突埋下了伏笔。
五台山的这粒大米,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宗教界“寺庙经济”的尴尬现实。
在地方政府政绩冲动与商业资本逐利本性的双重驱动下,宗教场所的生存逻辑早已被彻底改写。“第一财经”报道称,“寺庙经济已成为文化旅游产业中的高盈利板块,市场规模预计在2025年~2026年有望突破千亿”。但这片“千亿蓝海”背后,天价门票、强制消费、虚假开光等问题屡禁不止。某宗教景区门票价格曾高达230元;部分寺庙滥造露天大像,耗资动辄数亿元,远超宗教需求;更有甚者将寺庙资产打包,作为企业筹码进行资本运作。
在这种“政、商、教”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中,寺庙的围墙被资本推倒。
五台山的冲突,便是宗教场所在商业化浪潮中迷失方向的必然结果。而如何厘清宗教与资本的边界,已成为宗教反腐攻坚战中必须解开的死结。

一场攻坚战
2025年的宗教反腐,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公权力的深度介入与法律底线的重申。
过去,面对宗教界的问题,多采取教内整顿、注销戒牒等“清理门户”的方式,往往止步于道德谴责或行政处罚。而此次,司法机关直接入场。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对释永信的批捕,绍兴警方对道禄的刑事强制措施,释放出强烈信号:宗教身份不再是免罪金牌,教规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2017年11月,12部门就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禁止“将佛教道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打包上市或进行资本运作”。
2018年,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要求宗教场所建立健全“财务公开等制度”,接受监督管理。
然而,治理之路荆棘丛生,首先是“合法自养”与“商业化”的边界界定难题。宗教场所需要经济收入维持运营,合法的文创产品、素斋服务无可厚非,但“过度商业化”的标准似乎缺乏明确操作细则。
例如,某寺庙的“高考祈福套餐”明码标价:烧头香888元,挂祈福牌1888元,据说“能保佑考上985”。而这究竟是“合理服务”还是“营利性经营”,执法部门往往难以界定。这种模糊性导致部分场所打“擦边球”,将商业化行为包装成“宗教服务”。
这种不完善与利益链条固化,进一步加剧了治理难度。
宗教资产性质特殊,产权归属也混乱——有的寺庙归宗教团体管理,有的属文物部门管辖,有的被旅游公司实际控制,财务监管缺乏统一标准。
另外,许多寺庙虽有财务制度却形同虚设,功德箱收入、香火钱缺乏第三方审计,道禄的莲花慈善社甚至通过现金支付规避监管,善款去向成谜。
更棘手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商业资本与宗教场所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依赖宗教旅游拉动财政,资本方追求利润回报,寺庙则获得修缮资金,三者利益深度绑定,导致整治行动常遇阻力。
登封市政府曾计划将少林景区门票资产划入合资公司推动上市,而少林寺方面竟“一无所知”,这一事件正是利益博弈的典型写照。
互联网的发展更让监管面临新挑战。释永信通过直播带货,道禄利用网络塑造“慈善僧人”人设,电商平台上“开光手串”“线上祈福”等商品热销,虚拟空间的宗教商业化行为分散、隐蔽,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全覆盖。
一位统战部官员说:“宗教领域的腐败乱象,最终推动反腐行动走向深入”。这场风暴的核心并非否定宗教本身,而是通过制度重构斩断利益链条,守护宗教的纯粹性。
2022年实施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规定中,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主要包括的任务有:(一)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对本场所的财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二)进行会计核算处理,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实施财务公开,如实反映本场所财务状况;(三)合理编制预算,统筹安排、节约使用资金,保障本场所正常运转;(四)规范本场所收支管理,严格审批程序;(五)规范本场所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维护合法权益。
而多地推行的财务数字化改革更成为反腐关键抓手——宗教场所需使用统一财务软件,实行会计、出纳分离,功德箱由寺管会统一管理,重大支出需集体决策并报备,审计结果向信众公开。
“以前有的寺庙财务是‘糊涂账’,香火钱被少数人掌控,现在每一笔收支都有据可查,从源头遏制了腐败。”某宗教事务部门工作人员坦言。
更值得关注的是,宗教界的自我革新正在悄然发生。释永信涉刑、道禄被捕等一系列事件如同惊雷,唤醒了佛教界对商业化的反思。而治理的核心,在于让宗教回归本质——寺庙不是上市公司,僧人不是商人,信仰不是商品。
对于中国佛教而言,现在的风暴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它迫使宗教界斩断与资本的过度纠缠,重建戒律与自律,也让信众和社会重新认识宗教的价值,摒弃功利化的信仰观。
“这不仅是对佛教界的救赎,也是对每个追寻信仰者的回应。”上述宗教事务部门工作人员说。